《40堂哲學公開課》概括介紹了西方哲學發展的脈絡,探討了許多重大的哲學問題,如怎樣認識世界、什么是道德、什么是正義等。這是一部生動的西方哲學史,也是一部人類的思想史。閱讀它,像哲學家那樣工作、學習、思考、爭論,何樂而不為呢?
哲學一詞來源于希臘,其意為“智慧”。哲學家善思、質疑、爭論、實驗挑戰各種權威觀點,窮究各種選擇,力求促進人類科學和思想的發展。
蘇格拉底樂于為自己的思想爭辯,在辯論中產生大智慧,故有“蘇格拉底是哲學守護神”的說法。伽利略懷疑亞里士多德“較重的金屬塊下落更快”的觀點,在比薩斜塔用科學實驗向“確定真理的權威”亞里士多德挑戰,最終用實驗擊敗了“真理的權威”。笛卡爾的“懷疑論”認為不能完全相信自己的錯覺:如插在水中的筷子,從側面看上去是彎曲的;方形的塔,從遠處看上去是圓形的。“笛卡爾二元論”是對這個世界的獨特思考。
哲學家不是憑空產生的,也不會人云亦云,他們善問、善思、善疑,另辟蹊徑產生新學說、新思想。學習何嘗不是如此?
孟子說:“盡信書則不如無書。”明人陳獻章說:“學貴有疑,小疑則小進,大疑則大進。”學生善問、獨立思考、大膽質疑、肯于鉆研,能打破對權威的迷信,產生新見解,顛覆舊傳統。試想,若學生只是一味地接受書本知識,聽老師講,對書本觀點、教師的講解沒有一點懷疑,不能窮究其理,充其量只是“四腳的書櫥”,窮其終身也會無所創新、庸庸碌碌。
教學又何嘗不需要思考和懷疑精神呢?教師在學習、實踐中,反思自我、否定自我,才能不斷地提升自我、博采眾長;墨守陳規、抱殘守缺、畫地為牢,以老經驗應對教育改革,穿新鞋走老路,必將誤人子弟,愧對神圣的教育。
人生觀、幸福觀事關個人命運的發展,也與社會的進步密切相連。伊壁鳩魯提倡簡單的享樂主義,即人人尋求快樂,消除痛苦,善待周圍的人,欲望簡單則容易滿足,有時間和精力去享受更有意義的東西。波伊提烏認為:真正的幸福來自內心,是富足的精神狀態;財富、權力、榮譽都是毫無價值的,任何人都不該把幸福建立在如此脆弱的基礎之上。約翰•斯圖爾特•穆勒則寫道:“做個怏怏不樂的人,也比做頭心滿意足的豬要好;寧做一個不快活的蘇格拉底,也不要做個笑嘻嘻的傻瓜。”
在人類思想先驅、先賢圣哲的引領下,教育者應該有怎樣的幸福觀?教育的幸福在哪里?
孩子喜歡上學,學校成為學生向往的地方;學校是文化的圣殿,處處散發著濃濃的書香,師生沉浸在幸福的閱讀中;學校是學生思維發展的場所,逆向思維、發散思維、邏輯思維在課堂中形成。學生知書達理、品德高尚、喜歡讀書、思維嚴密,積極參與學校生活,臉上燦爛如花,教育能不幸福嗎?
學高為師,身正為范。沒有教師的幸福豈能有學生的幸福?幸福的教師精神豐富、志存高遠、追求卓越,在教育事業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;教師甘為人梯、默默奉獻,學生的成長就是自己最大的幸福;幸福的教師熱愛閱讀、博學多識,在閱讀中汲取前行的力量;幸福的教師胸懷坦蕩,悅納好孩子也悅納有缺點的孩子。
如今,我國教育正處在轉型期,專家學者為我們提供科學的教育理論和先進的教育模式,但究竟如何傳授文化、教育孩子,還要靠教師智慧嘗試。有人認為,教育改革成效如何,關鍵要看教育行政部門的頂層設計。不錯,頂層設計不可忽視,但一線教師才是教育改革的親歷親為者,他們的言談舉止、情緒好壞會直接影響孩子的學習效果。
一個人遇到好老師,是人生的幸運;一個學校擁有好老師,是學校的光榮;一個民族擁有一批又一批好老師,是國家的希望。誰能拯救教育?唯有幸福的好老師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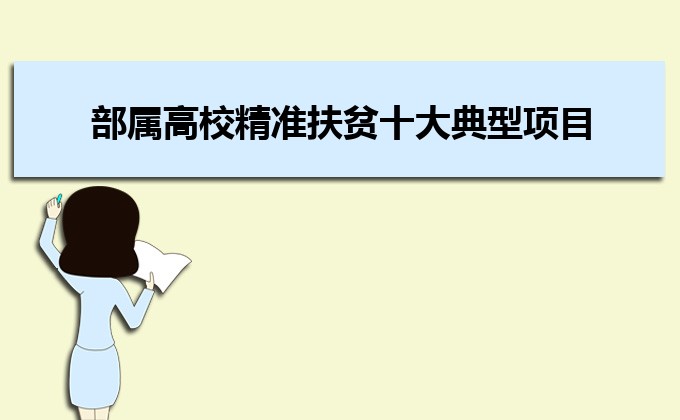 部屬高校精準扶貧十大典型項目掃描
部屬高校精準扶貧十大典型項目掃描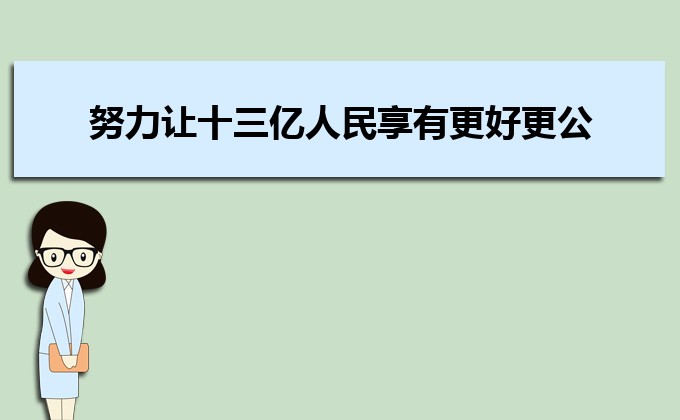 努力讓十三億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
努力讓十三億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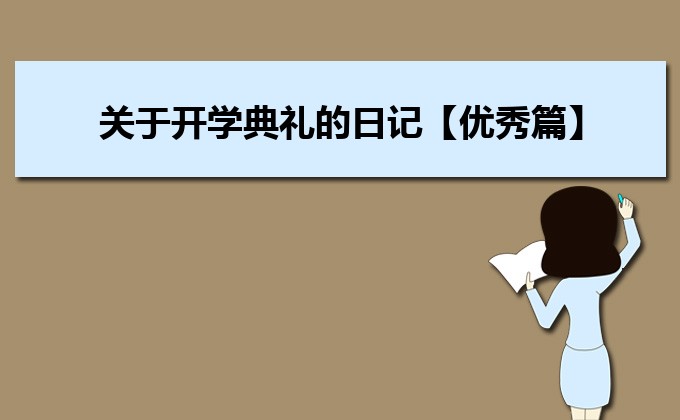 關于開學典禮的日記【優秀篇】
關于開學典禮的日記【優秀篇】 河南大學生就業創業人數“雙增長”
河南大學生就業創業人數“雙增長” 為什么不建議孩子去私立學校 有什么壞處
為什么不建議孩子去私立學校 有什么壞處 云浮私立學校名單及排名最新排行榜
云浮私立學校名單及排名最新排行榜 揭陽私立學校名單及排名最新排行榜
揭陽私立學校名單及排名最新排行榜 潮州私立學校名單及排名最新排行榜
潮州私立學校名單及排名最新排行榜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