語文教材中的“假課文”,近期引發持續討論,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,說明大眾已經開始自覺地檢視語文基礎教育水平。其實,假課文是個案,比假課文更多的,是“水”課文??語文教材中體現的文化含量不足、中華文化精髓不足,讓很多語文教材有了“白開水”似的觀感。
回顧中國教育的歷史,我們不難看出,中國一直有著重視經典的教育傳統。直至上個世紀前期,許多人仍然是自幼即閱讀中國文化中的那些最重要的著作??
歷史學家顧頡剛3歲時,母親就開始教他讀《三字經》、《千字文》,四歲時叔父即教他讀司空圖《詩品》,5歲時就開始讀“四書”、“五經”。文史專家錢基博9歲讀完了“四書”、《易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春秋左氏傳》、《古文翼》,而且皆能背誦。文學家夏?尊10歲前讀了《左傳》、《詩經》、《禮記》。歷史學家周一良8歲在家塾讀書,學習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詩經》、《禮記》和《左傳》。這些學者童年、少年所讀的這些著作,為他們后來的進一步學習的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
那一時期,民間的普通人也往往知曉中國文化中的重要經典。國學大家姜亮夫年輕時從云南到四川,發現四川之地文風很盛。后來他在“憶成都高師”一文中說:當時四川的農人非常勤苦,“早晨雞叫就下田,一有閑空,躺在草堆旁一面曬太陽,一面讀詩、學《論語》。文化已滲透到田頭,所以民間的對唱、詠詩很普遍。民間讀五經、四書也很普遍。去峨眉山的路上,抬轎人前后對答往往有詩句,尤其是唐詩。”
兒童、少年時期閱讀《論語》等經典,能夠讀懂嗎?今天人們對此不無疑問。對此,金克木在《書讀完了》一文中提出自己的看法。他首先認為,“五經”以及諸子經典是學習中國文化的基礎,不讀這些著作,就難以真正讀懂后來的書籍,并進一步說道:這些書,除《易》、《老》以外,“大半是十來歲的孩子所能懂得的,其中不乏故事性和趣味性。枯燥部分可以滑過去。我國古人并不喜歡‘抽象思維’,說的道理常很切實,用語也往往有風趣,稍加注解即可閱讀原文。一部書通讀了,讀通了,接下去越來越容易,并不那么可怕。從前的孩子們就是這樣讀的。主要還是要引起興趣。孩子有他們的理解方式,不能照大人的方式去理解,特別是不能摳字句,講道理
。大人難懂的地方孩子未必不能‘懂’。”金克木的話,非常富有啟發性。
上個世紀前期的一些學人的閱讀實際,也印證了金克木所說的話。如顧頡剛7歲時開始讀《左傳》,他回憶當時的閱讀感受時說:“我讀著非常感興趣,仿佛已置身于春秋時的社會中了。從此魯隱公和鄭莊公一班人的影子長在我的腦海里活躍。”關于詩經,顧頡剛這樣說:“我讀《詩經》,雖是減少了歷史的趣味,但句子的輕妙,態度的溫柔,這種美感也深深地打入了心坎。”自然,小學生閱讀經典,對經典的內容不可能完全理解。但這其實是沒有關系的。孩子能夠有所感受,有部分的理解也就足夠了。更多的理解,是留給未來歲月的。語文是基礎,這所謂基礎,應該理解為人的整個一生的基礎。語文教材所選的文章,應該是那些值得人一生回味和思索的作品。不值得回味的作品,其實也是不值得學習的。
相比之下,今日的《語文》教材中,中國文化含量不太夠。北師大童慶炳教授曾提出建議,他認為小學生入學,即可以學習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:“假如小學一年級教材的第一句是孔子的‘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’,那么孩子們就覺得一跨入學校的門檻,就與現實的世界不一樣,就似乎一下子進入了‘學問’的‘深處’,他覺得深奧,覺得困難,覺得陌生,覺得不易理解,但同時覺得有意思,有興趣,有挑戰,這會極大地提高他對學校的認識,對學習的認識,極大地提高他學習的積極性。”這是很有道理的。
孩子學習的內容,應該是有一定難度的。兒童對那些自己完全能懂的東西,也是沒有什么興趣的。他會覺得,這樣的學習內容沒有味道。孫紹振上小學時,教材上的課文是“喜鵲叫,客人到,媽媽去買面,面上一塊肉,客人吃了點點頭”之類。對這樣的課文,他的感覺是:“一點味道也沒有,白開水,幾乎全是廢話。”當時,他母親教他的詩歌是:‘昨日入城市,歸來淚滿巾,遍身羅綺者,不是養蠶人。’以及“寒夜客來茶當酒,竹爐湯沸火初紅;尋常一樣窗前月,才有梅花便不同。”這樣的詩歌,對于剛上小學的七八歲的孩子而言,未必是完全能夠理解的,但他卻對這些詩歌更感興趣。有一定的難度,孩子才會“覺得有意思,有興趣,有挑戰”,有學習的積極性。
近日來,語文教材中的一些課文如《愛迪生救媽媽》是“假”課文,這引起人們的關注和爭論。語文教材中確實有一些“假”的課文,但這還不是最大的問題,最大的問題是太簡單,特別是,課外的文化含量太低。《愛迪生救媽媽》一文有500多字,告訴學生的不過是:愛迪生是個聰明的孩子,我們應該向愛迪生學習。這500個字,還不如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這8個字更有教育的價值。文化的含量低,特別是中國文化含量嚴重不足,是當前語文教材的一大問題,這一問題不應再被忽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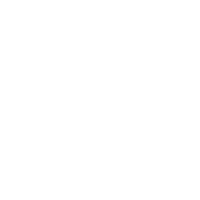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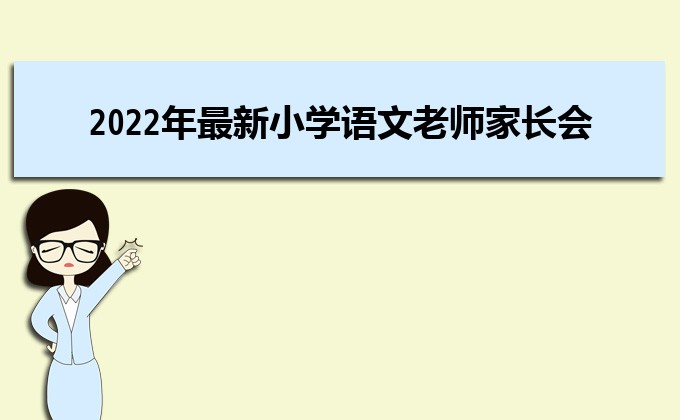 最新小學語文老師家長會發言稿范文
最新小學語文老師家長會發言稿范文 小學語文高效課堂心得體會
小學語文高效課堂心得體會 小學語文信息技術應用體驗心得體會_精品
小學語文信息技術應用體驗心得體會_精品 小學語文信息技術應用體驗心得體會范文
小學語文信息技術應用體驗心得體會范文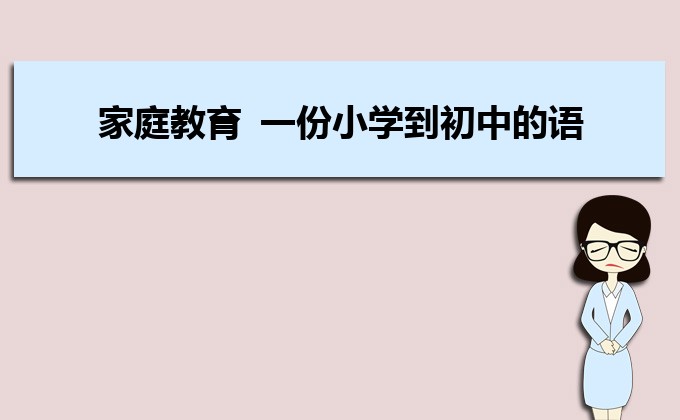 家庭教育 一份小學到初中的語文學習規劃
家庭教育 一份小學到初中的語文學習規劃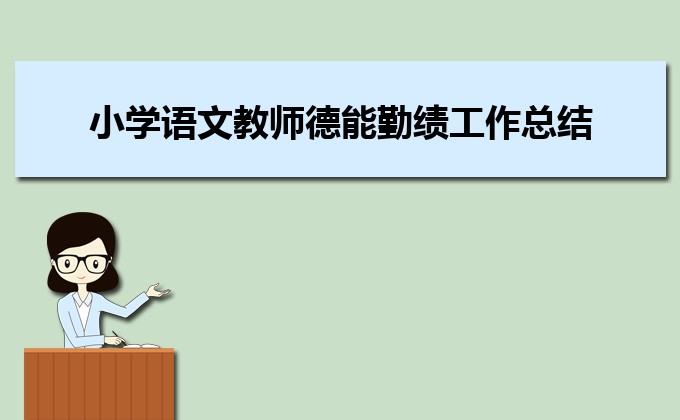 小學語文教師德能勤績工作總結
小學語文教師德能勤績工作總結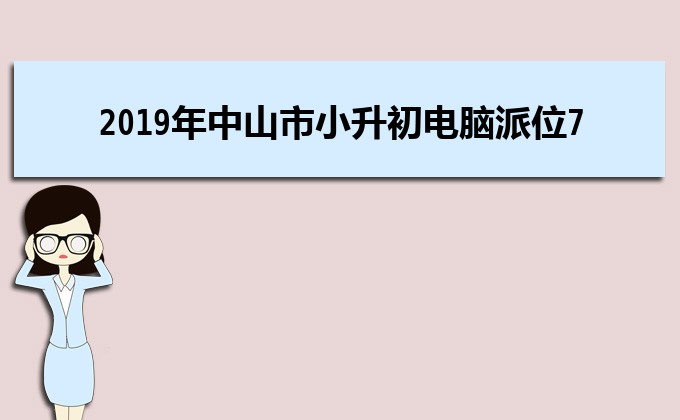 中山市小升初電腦派位7月5日舉行
中山市小升初電腦派位7月5日舉行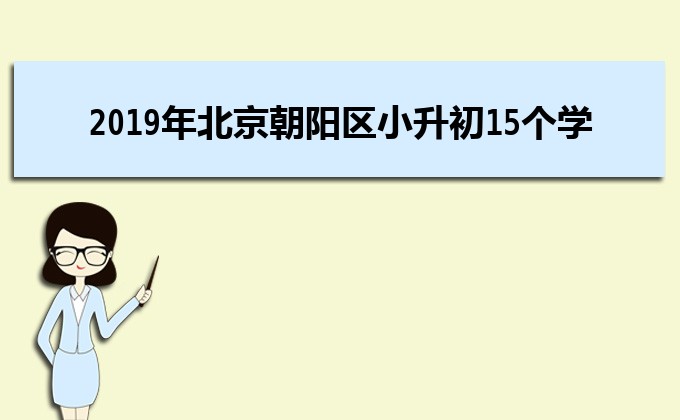 北京朝陽區小升初15個學區劃分不變
北京朝陽區小升初15個學區劃分不變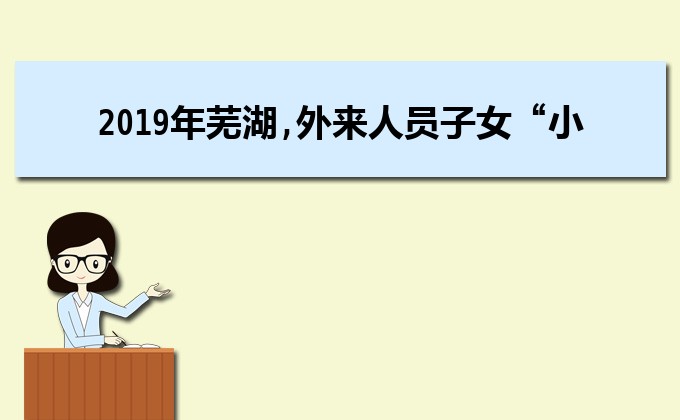 蕪湖,外來人員子女“小升初”4月30日前辦好居住證
蕪湖,外來人員子女“小升初”4月30日前辦好居住證 玉林小學入學政策年齡條件報名條件具體有哪些
玉林小學入學政策年齡條件報名條件具體有哪些 貴港小學入學政策年齡條件報名條件具體有哪些
貴港小學入學政策年齡條件報名條件具體有哪些 欽州小學入學政策年齡條件報名條件具體有哪些
欽州小學入學政策年齡條件報名條件具體有哪些 防城港小學入學政策年齡條件報名條件具體有哪些
防城港小學入學政策年齡條件報名條件具體有哪些











